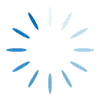刘彻收敛了笑容,定定的看着他,说:“娇娇,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是真的吃定我了。”对他如此的无情,他已经是她的夫君,还有什么好坚持的?这样下去,对她有何好处?
阿娇抬头,看着他的黑眸,他的眸子幽深不见底,想从中找出他的情绪,比登天都难,当然皇帝这种人,是所有人中的人精。
她早就放弃猜测他的想法。还不如直接问来得快:“太子为什么这么问?我难道有不妥之处吗?”
不妥得很。第一个女人,第一个爱恋的对象,竟然冷淡的问他有何不妥?刘彻伸手捏着阿娇光滑的下巴,说:“娇娇,你并没有将我当作你的夫君,这就是最大的不妥之处。”
“我自然当你是我的夫君。”阿娇表情未便。只是他不再是她的爱人。
“哦?既然如此,我为何没有看到你眼睛中的喜悦?”她没有妻子对夫君的醋意,也不相信他会为她出头。
阿娇嘴角拉长,眉眼弯弯。笑还不容易吗?
刘彻猛的上下其手,将她柔嫩的脸捏到了一起,说:“刚刚丑死了,现在正好。”
“你……杭开。”阿娇语词不清的说,一边使劲的拉下刘彻作乱的手。刘彻这厮脑子被驴踢了吧,疼死她了。
刘彻作弄够了,看着阿娇纠结的脸庞,这才放手,心高气爽的说:“这样才算正常,你平常那一副样子,还以为你别的表情没有了呢?”
阿娇站起来,抄起身边的铜鼎,就向刘彻砸去:“你这个死小猪,去死吧。”这人太可恶了,谁想一直一副表情,她是被谁害的。
刘彻偏过头避开,跳到旁边,笑着说:“这样才像娇娇嘛。”这是另一个杯子被扔过来,他接过,继续说:“娇娇,我说你在未央宫有什么好怕的?我总归不会让你委屈的。你是不是在生气我没有当场反驳刘陵?其实……….喂,你还来真的啊,这么大一个铜鼎你也扔过来。!”
终于刘彻不耐烦玩了,他逮住机会,一把将阿娇抓住按在榻上,使劲的吻住她那张伤人心的嘴。
一如往昔的甜蜜和美味,她水汪汪的杏眸因为刚才的一番动作平添了姝色,水汪汪的,闪亮亮的,让他的心也跟着动了起来,动作也越发的大了起来。
阿娇挣扎不得,只能任由他施为。在迷糊中突然想起他未尽之意,忙努力的清醒头脑,说:“刘彻,你刚刚说你没有当场反驳刘陵有何深意?”
刘彻恼怒,立即堵着她的嘴,动作幅度更加大了一些。难道一个刘陵也比他重要吗?可恨的陈阿娇!
亏他还特地将程氏引出来,免去她被父皇猜忌的危险,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
阿娇吃痛:这个猪头是属狗的,竟然咬她的肌肤。但随即而来的酥麻让她没有了时间思考。
知道第二日,她再问题的时候,刘彻只是用一种你是白痴的表情看了她,然后飘飘然的说:“这么复杂的事情说给你听,你也是想不出了。还不如留着脑子好好想想怎么将东明殿事宜弄好。”
阿娇叹了一口气,太子妃不光是一个称呼,还代表着权势。东明殿的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局、尚寝,还有大长秋都是需要有人来担任,这是她进入未央宫的第一重考验。虽然这些事情前世已经轻车熟路,但还是需要时日去做,那就慢慢来吧。宫里的生活,不就是那样吗?
阿娇在未央宫开始太子妃生涯的时候,刘陵已经顺利的回到了寿春。可是迎接她的不是亲人的思恋和痛心。
刘安狠狠的甩了她一巴掌,刘迁和刘不害则在旁边恨恨的看着她。
刘陵甚至不敢去抚摸自己发烫的脸颊,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楚楚可怜:“父王,是陵儿鲁莽了,求父王恕罪。”
她知道她犯了错,首先请罪才是最重要的。
刘安气哼哼的坐在大厅中央,说:“陵儿,枉费为父一直培养你,甚至超过了你的两个哥哥,可是你回报给我的是什么?是降爵。为父老了倒不在乎,可是你两个哥哥怎么办?难道和那些普通人家一样拼性命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侯府爵位吗?我们可是高祖直系子孙。”
刘迁冷笑一声,说:“只怕妹妹只记得情郎,早就忘记父王的嘱托了,何况我们这些做哥哥的呢?”
刘陵并不争辩,抬起头,眼睛灼灼,说:“父王,我在长安发现了一件大事。”
第37章
刘安还没有说话,刘迁一下子冲过来,照着刘陵就是一脚,很恨的说:“就是因为你的私心,才害我父王和我们,你还想怎么狡辩?”
刘陵心口一痛,直接咳吐了一口血,这就是她的亲人,遇事只会推到她的身上。以前因为她他们得到了长安那么多贵重赏赐的时候怎么没有见他们有怨言?
她真是恨,恨她是一个女儿身。只能做两个草包兄长的踏脚板。也恨他怎么就看上了刘彻那个无情的人。她哪里比陈阿娇差?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头看一眼她呢?
可是他真的好有男子气概,不像她周围的那些男人,遇事畏畏缩缩不说,还要依靠女人的裙带,无耻。
她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让刘彻爱上她。那么第一步就要他正视她的存在。
擦掉嘴角的鲜血,看着刘安,她一字一句的说:“父王,皇帝只怕命不久矣。女儿判断他恐怕只有年底的寿数了。”
刘安立即震惊了,刘迁和刘不害面面相觑,要是刘陵说的是真的,也的确是一件大事。但是长安城根本没有半点动静啊?会不会是她想脱罪编出的谎言?
刘陵看到他们的申请,就知道他们的心思,心里很不屑,但面上还是恭敬的说:“父王,请您相信陵儿的话,我绝对不会看错的。也不会害您的,这与我没有半点好处。”
刘迁阴阳怪气的说:“怎么没有半点好处?有了你的投诚,说不定刘彻一高兴,你就得偿所愿了呢。”
真是受不了这个妹妹,喜欢谁不好,非要喜欢刘彻。父王的脸都让她丢尽了,可是父王还是相信她多于他。漂亮人就是这么占优势。即使在这样狼狈的情况,还是这么的美丽,让他的心都有些躁动起来。
但是这样的心情立即被他压了下去,现在还不行,他还只是一个世子。
刘陵看到他眼睛的猥亵,心里一阵翻腾,她必须尽快壮大自己的实力,否则以后她绝对生不如死。
想到这里,她的泪一下流出来了,哽咽的说:“哥哥,我生是淮南的人,死是淮南的鬼。即便我和刘彻虚与委蛇,也是为了淮南着想。哥哥难道不知道,淮南早就成了皇帝的眼中钉了吗?从周亚夫节度扬州刺史部,到现在的陈宏都是皇帝的亲信。并且现在父王的军政大权只怕马上就会被陈宏收缴,下一步不光连侯爵都不一定保得住,只怕我们一家也难逃劫难。还请父王早作打算。”
刘安皱着眉头说:“陵儿,你是不是想多了。扬州刺史部本就是全国最重要的刺史之一,皇帝排亲信也不奇怪。但要说对付淮南我却有点不相信的,毕竟大家都是高祖子孙,除国已经是大惩处了。”
刘陵心里有些瞧不起刘安的面子光,既然大家都是高祖子孙,父王私自造那么遁甲,养那么私兵,难道就是为了好看吗?但他是淮南的王,在文人中又一向有威望。她必须靠他,才能让自己不落入悲哀的境地。
狠狠的咬了一下嘴唇,她头触地,深深的拜了一礼,说:“父王,我以母妃发誓,我在长安的细作拼死送出的消息,只要不出事情,皇帝计划两年之内解决淮南。女儿这么出事,只怕也是皇帝对付淮南的前奏,否则岂能会这么一点小事就怪罪父王?”
刘不害实在听不下了,冷冷的说:“一点小事?陵儿,我看是你一直在狡辩。你打了陈阿娇的脸,刘彻能高兴?你以为你是谁?刘彻觉得没有丢脸,皇帝能有脸面?何况皇太后对馆陶公主母女的偏爱是举世皆知的。你这不是找死吗还顺带连累了父王。”
其实最主要是连累了他。他一个庶子本来前景就不明朗,现在只怕更加只有被放弃的命。刘陵安安稳稳的当翁主就好,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事情。
刘陵并不回答刘不害的话,他们只知道和她争,自己半分能力没有。要不是她命不好,她怎么会只是翁主?况且有谁有她了解父王?
父王的心思早就不纯了。要不然也不会花大力气编纂一本《淮南子》,还不是为了收拢人心?一个诸侯王收拢人心做什么,还不是为了更上一层。
所以刘迁和刘不害的意见,她并不在意。她只需要说服她父王即可。
刘安也在思考,刘陵最在意的就是她的母亲,之所以放心的用她,也是因为她有把柄在他手里。她不会背叛他的。当然也实在因为两个儿子不争气,远远不如刘陵。所以他才对刘陵一些权柄。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