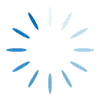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
“瞧!”浮玉得意地扬起脸来,“是不是一模一样,我许早便见过这……”
像是在与画中人眼眸相触的一瞬,灵魂便似坠入那幽邃的沉潭之中,雩岑呆愕着,世界空响,仿佛霎那间屏蔽了所有的声音。
意识仿若均匀地散布在每一寸的空气中,她却乎看见了那浮玉恣意盎然的面貌与张合不停的小嘴,却没有听见任何话语。
空气仿佛被凝滞。
磋磨的时间像是在某个时间点被无限拉长,她瞧见浮玉翕张的小嘴仿若一帧一帧的慢动作回放,身体却无法动弹。
她什么都听不见。
“阿岑。”
不知多久的沉寂,安静得像是走到了世界的开始与尽头,一道声音突而响起,远远地像是从天边传来,又近得,仿若贴着她的耳廓。
“时间的尽头是什么?”
她无法回答。
抑或是,就算可以,她也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种虚无飘渺的疑问。
那声音轻笑了一下,继而又问:
“时间又是从何处开始?”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如鼓擂锤。
“我从哪来?又要到哪去?我爱的人是否爱我?爱我的人我又是否爱着他们?”那道声音一字一句,忽远忽近,仿佛漂浮在梦里:“那么,我又是谁?”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那道声音似乎一直含着笑,浸透了数万年来来往往的月色与清风。
“还记得我与你说的么?”
“若是你想不通了,便朝着那片海浪走,朝着海上永恒的月亮走。”
“…那里有什么?”
却乎恍然的,她开口问道,怔愣间似乎就连自己都未反应过来,声音沙哑得可怕。
“有答案。”
“有你一直想要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不是么?”
还是那股熟悉的香味。
这却乎是她曾经闻过的,在哪个梦中,却一时想不起。
那是被清风融化的月色滴入池塘的声音。
“遗忘…回溯…还是终究,成为你自己……”
“只要…跟着…….你…的……心…….”
渺远而清澈,却似入梦春风般地忽而消散,雩岑尚还未反应过来,那压迫耳膜的触感却忽而消散,耳边继是响起的大喊大叫将她激得险些跳了起来。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全身的汗毛瞬间直立而起,雩岑吓得跳开一步,差点将面前长案上的青灯撞翻。
“……啊???”
“我叫了你半天都没回应,莫不是因六叔的墨宝看呆了神?”浮玉嘟嘟嘴,悄咪咪抱怨道:“现下你可相信了罢,我才没有认错人!”
“你就是荼姑姑!”
小丫头的声音斩钉截铁,雩岑的关注点却依旧是颇为奇特,愕然地重复道:“…六叔?”
浮玉点点头。
“我听娘亲说,这本是六叔当年在时的书斋,后来便废弃了。”
“他留下的东西几乎都被精心分类整理了一番,比如你瞧——”小丫头回身指向那墙角处高垒的油纸包堆,“那些便都是六叔在时的一些藏书,我爹爹整理收藏了大半,但一些还未来得及探看内容来分类,再加上他公务繁忙,久而久之便忘了去,之前还是我想要深学些卦法之数,他才同意我来这儿的。”
雩岑听着耳边的话,却是忍不住垂眸深觑那长案上的画,这却乎是她第一回,真真切切一睹那神荼的容貌。
说过她与神荼相像的人有很多。
白泽、零随、韩灵…还有那确确实实见过神荼的零郁……
一如雩岑有时还会好笑地遐想,其实这不过是他们多年记忆磋磨之下的错认,或许她与神荼有着八九分的相像,但到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如今那画像上弯眸浅笑的女子,却仿佛瞬间冷冷地对她泼了一盆冷水——
若非那画像坠尾标写的神荼之名,换作与她相识相知千年的颦瑶,恐怕都认不出有何不同,甚至连她自己方才的一瞬都下意识地认为…画像上的人的确是她。
真是…太像了。
她突而想起白泽第一次与她确认这件事的神情。
任凭是寿达十数万年的神,面对一个已然死了数万年之人活生生站在面前,换做她恐怕也会是那般的神情。
这是一副相当简单的画。
书斋微敞的门棂后,一个浅青衣裙的女子正杏眸弯弯地半掩着身,像是故意想捉弄人般从门扉间歪头探出一个小脑袋来,却遮不住怀里抱着的一捧黄花,还有连着枝干整小支折下的露水青梅。
“露浓花痩,薄汗轻衣透…和羞走,倚门回首…”雩岑愣愣地抚上那已然发黄的页脚上侵入每一道纸痕的浓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那落款之处,盖着一方小小的印章,甚至没有多余的缀饰,简单得,便只有唯余的两个字。
“…玄桓。”
是…
他吗。
不知为何,她猛然想起之前被零随剿杀之后,意识混沌间,所做的那一帘梦。
信水廊桥畔,那痛苦捂着腿缓缓跪坐而下的身影…
“其实府中还有大伯、二伯留下的库房,只不过爹爹一直不准我去看罢了,四叔五叔的东西整放在七叔那儿,唔,还有八叔…听爹爹之前说,清微府七八万年前好似无端起了一场大火,存放八叔东西的库房倒是没烧到,但后来好似还是都挪去了七叔那保管。”
浮玉自顾自絮絮说着,未曾去注意雩岑的表情几何,话音方落,便见那兀自轻轻抚着那画的人影站起身来,回眸问道:
“我能…随意看看么?”
“唔…这……”像是没料到对方如此要求的浮玉略略愣了愣,却还是点点头答应了:“姑姑的话,自然可以。”
雩岑起身环顾四周。
却未曾见到身侧浮玉的几不可见地、有些担忧害怕地的往外望了望,深深咽了咽口涎。
小姑娘没有去看那些箱子,而是鬼使神差般地走向了那高得几乎要垒到顶上的油纸包。
“这都是有分类的…”见着雩岑想要去碰,浮玉赶忙上前几步主动将其中一个油纸包的面挪正:“这包大抵是六叔在时的公文,那包是杂书,还有是我上次找的六爻卦法…不知姑姑想看哪些?”小丫头说着说着有些垮下脸来:“若是都弄乱了,被我娘抓到可就惨了。”
“那是什么?”
浮玉帮雩岑主动打着下手,生怕对方一失手倒霉的便是她,谁知对方却径直指向了数个大大油纸包最角落,某个隔着有些距离像是被遗忘的一个偏小的油纸包,小丫头闻言探手取来,却足足将其周甚都寰转着掉了一个圈,也没见上面有任何标注。
“欸?…奇怪…”浮玉疑惑地挠了挠头,嘟囔道:“这个怎得没有标记?”
然还未等到雩岑说些什么,小丫头便是眼睛一亮,颇为兴奋地双手并用,主动拆起包装来:“里面一定有什么好东西!”
须臾之后,便听得一声失望的哀嚎。
四道目光汇聚之处,不过是一迭已然泛了黄的信纸。
打开第一张空置的封面,其抬头赫然大大的写着叁个字——
检讨书。
………
浮玉在瞧见一打被钉装起来的厚厚信纸后便百无聊赖跑开了去,自顾翻出书库里的又一本六爻坐在一旁读了起来,而雩岑借着这个相当长的空档,几乎略略地将那厚厚一本的检讨书都读了过去。
是的,厚厚一本被钉装而起的,全都是所谓的检讨书。
无论是将那大小各异的纸细细裁填成整齐的书页,抑或是统一钻上小孔一层一层地细细缝制,这显然是个很细致的活,更不必说那按照落款时间顺序从头到尾的整理,笔者一开始的字迹虽青涩难看,翻到最后倒也像模像样了。
雩岑也是接近翻到最后,才认出那并非用原灵古语写下的落款是何人——
神荼。
原灵古语与当今上下界通用之语显然更为简练深奥,有些字虽同型却不同音,同音又不同意,好在她在昆仑到底学了些半吊子知识,一开始字丑的虽通篇难懂,到后面字形规整后倒也能猜出一些内容。
而其间大概有两叁次,似乎都是因为签一份的检讨不够诚恳有些糊弄,被打回重复再写,导致好几份的日期落在了同一日。
然其下更厚的一打更是让人震惊,一些却乎是神荼平日上交的作业,而更大一部分,却完全是罚抄。
雩岑随意翻了翻,单坤卦八宫图,便反反复复罚了将近一百张。
…这是她头一回同情一个神。
这也太惨了。
她还犹记自己在昆仑时因为作业忘交被某个古板秃头老仙罚了五十遍学律之事,到最后抖得连毛笔也拿不稳,简直时边哭边骂边哀嚎着交上了那厚厚的一打。
那足有她膝盖高度的罚文…这是抄了多久哇……
小姑娘缩了缩脖子收回手,然方要将蹲的发麻的小腿站起,脚尖一晃,发麻的腿肚一时使不上力,整个人竟扑头盖脸将那摞厚厚的纸整个撞塌了去。
散乱的纸页漫天飞舞,她听见了浮玉的哀嚎。
雩岑半晌才从深埋的纸堆里头晕脑胀地钻出身来,恍然间,似摸到了一根什么硬硬的玩意。
那漆黑的板身,冰凉的触感,还有那半臂长的长度——
“跪下!伸手——”
像是幻听,小姑娘吓得花容失色,下意识当啷地将手中的戒尺烫手般地甩出了好远。
“姑姑…”
浮玉哭嚷嚷地从同样的厚纸堆里探出头来,刚要说些什么,雩岑却又不知踩滑了什么,一个脚崴又向身侧堆迭了几块无用的额匾处撞去,小丫头不忍直视地、绝望地捂住了眼睛。
“浮玉…”
“啊?”
“这里,是不是早就封死了?”
“当然,当年为了防尘防潮,我爹爹特意叫人将这一切都……”浮玉说到一半的话语愕然愣住。
两人所望之处,那几块被撞翻遮挡的匾额后,竟鬼使神差打开了一扇门。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