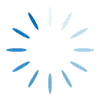睁开眼睛,刺眼的灯光照得她又闭上双眼,一股浓厚的医用酒精味,让陈若初觉得有些刺鼻。
「姊,还好吗?」陈若泽凑近身,一股古龙水的味道衝击而来。
「陈若泽,你是把古龙水当花露水喷吗?」
睁开眼,面前梳着油头的老弟,古龙水的味道让她突然又觉得一阵头晕。
「你真的很夸张,生病是不会跟我说一下吗?我昨天晚上到今天,打了几十通电话,结果一接通就跟我说你人在医院——」
「人都倒了要怎么说?」受不了陈若泽连环炮的碎碎念,她抬手直接压住他的嘴,点滴管扯了一下,她眉头微皱瞧了一眼悬在头上的点滴瓶,「所以你刚才有看到一个女生吗?提着一个宠物袋。」
陈若泽听闻,翻了个大白眼,抬起手臂指了指自己手腕的錶带,翻过去睹着陈若初眼前让她看个清楚。
他挪开脸,扒开陈若初堵嘴上的手,鼻翼抽动了几下,一副死鱼眼的样子看着陈若初。
「你知道你昏过去多久吗?整整一天!人家慈恩姊今天要上班,小猫她先带去兽医院了......」说着像是想到什么,陈若泽打岔道:「对了!桐希姐的喜帖寄到家里来,我就先代收了——她是不是不知道你搬出去住了?」
「嗯......她不知道。」
她甚至没发觉这些年来的刻意疏离,陈若初还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狠。
是挺狠的,有段时间身边朋友都以为自己得了忧鬱症。
陈若初打开手机,平常催得要死要活的蔡老闆没有打电话给自己,桐希的讯息停在那两则未读,她看了没点进去,只有不断跳出讯息的公司群组,才有了自己真的在医院睡过一天的实感。
「然后慈恩姊让你醒来跟她说一声——话说,她是不是你高中同学来着?」
「你怎么记得比我还清楚?」她停下手上的动作斜睨一眼陈若泽。
「要你管,」他说着捂上自己的肚子,微微垂下嘴角,「姊——我饿了。」
「......你打电话只是想蹭吃的吧!」
「不是啊!你得理解我,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下午四点多了,我一口正餐都没吃,只吃了从酒吧拿的花生坚果——」
「酒吧?!」
「别跟老爸告状啊,我上次喝断片的事被他知道,在你家睡多久你知道的。」
「......你可以滚吗?」她揉着太阳穴突突跳着的青筋,感觉陈若泽的出现根本是让自己病情雪上加霜。
「我想吃你公司附近的那家烤肉~」
陈若泽舔了舔唇,搓了搓手,期待的眼神让陈若初只想把他踢出去。
怎么会有人这样要求刚醒来的病人带自己去吃东西啦!
思索着最近有什么理由能让自己情愿带这臭老弟去吃,陈若初思来想去发现的确有这么一个理由。
「这次班排多少?」
他顿了一下,唇角勾起,神气的抱着胸说:「哈哈!全班五十人,我排第十!」上扬的嘴角得意的让陈若初无奈的看着他。
「难怪你会打给我,只有邀功跟避难才会想到你这个姊姊。」她冷哼一声,还是拿起手机查起那家烤肉店的营业时间。
「嘿嘿,所以成交?」
「......成交。」
「喔~你最好了~大方、心善、人是长得还行啦,其他优点补足这个缺点......」
陈若初叹了口气,要他别再说下去,陈若泽倒老实,真乖乖地闭上嘴,起身找护理师开单去了。
拿了药,陈若泽拿着估价单去缴费,要陈若初先去大厅等自己,陈若初看他拿着手机在耳边说些什么,快步离去的背影,竟觉得和小时候望着父亲的背影有几分相似。
那时,父亲的背影就像自己的保护墙,把一切困难都挡在她未闻未见的墙外。
只是陈若初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会站在墙外,不论怎么喊都不会有人回应。
拨通电话,陈若初用左手拿起手机放到耳旁,视线停留在自己多灾多难的右手上,手背拔针贴的OK蹦,和虎口的纱布粘到了一起。
昂首凝视着挑高三层楼的天花板,垂吊在空中的压克力装饰和轻摆的祝贺布条,镶嵌在墙上復古的大鐘,下方还有台黑色的三角钢琴被红龙围绕起来。
一旁坐在母亲腿上玩着什么手机游戏的小孩子,让她脸上留下一道不深不浅的笑容。
母亲笑得和蔼凝视着孩子的面庞,整理着他的头发,偶尔会参与到孩子的游戏之中,孩子也会笑得开心和母亲一起玩,头头是道的解说着玩法,抓着母亲的手一步一步的按着,脸上得意的神情,是孩子独有的天真骄傲。
「若初。」于慈恩的声音打断了持续数秒的嘟声,闯进她的耳里。
电话意料外地接通,本以为会随着时间结束,传来的会是稍后再拨的机械式女音。没想她在最后一刻接了起来,这让陈若初突然有些措手不及,婆娑着袖口角线头的手顿了一下,嘴里支支吾吾想了半天没凑出一句话。还忽然想到自己对她那或许有些过分亲暱的行为,脑袋一下就整片空白掉,没发现自己耳根瞬的红起来了。
「嗯...昂...我醒来了。」这句话可能是耗尽自己当下所有的语言组织能力,所拼凑出来。但语气还是有些许的生硬、不自然。
「好,那你早点回家休息。」
于慈恩的声音听起来没有特别的改变,还是温温柔柔。
这让她有了勇气想要开口提起那天发烧而诞生的蠢事。现在光是想到,陈若初都觉得羞愧万分,又是抓头,又是摸脸,口水抿了又抿。
「还有昨天的事——」
「经理我有事想请教一下......」
听见于慈恩身旁好似传来几位男性的声音,想说的话卡在嘴边,听见于慈恩离话筒稍远,浅短的话音断续的传进通话中的手机。微啟的唇齿合了起来,她上齿轻咬着下唇瓣沉默。
感觉自己好像又打扰到她工作。
道歉的话陈若初没有说出口,而是将手臂缓缓放下,逕自地将电话给掛断了线。
陌生的失落感围绕在她的心里,陈若初不解自己那种不是滋味的落差,是从何而生,从何而来。
大厅那座没人能触碰的钢琴,因为整点时刻,自顾的敲击音弦,响起了优美的乐音。来往的人群,驻足欣赏了一阵,再次匆忙而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