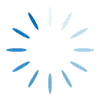萧景并没有问为什么,而是说,“有这么想她死?”
她摇摇头,表情冰冷,“事实上,我并不想。”
死不能解决问题,而恨一个人不是要他去死,而是让他活着,最好是痛苦的活着,这样才能达到令她痛苦的目的。
男人寒冷料峭的深眸里酝酿出点点笑意,看着她,“我以为你想。”
安言低头,唇上有着让人看不清的弧度,萧景将她抱在自己怀中,闻着她身上的味道,心里安宁不少,“现在还早,茯苓还没过来,要不要先上去睡一觉?”
她有些抗拒,怔怔地看着自己的手指,“我怕我会做噩梦。”
这话她没说错,她是真的害怕做噩梦。
但是不管她说什么,男人已经将她打横抱了起来,眼中染上浅浅的笑意,“我不勉强你,睡隔壁次卧?”
没想到他能这么直接,安言猝不及防,还是吓着了,抬手搂住他的脖子,有些抱怨,“你做什么?”
萧景沉沉地笑,“抱你上去休息。”
安言感受着自他身上传来的温度,闭了闭眼,“我比较想回自己的家睡。”
说完,她明显感觉到抱着她的男人身形微微一顿,兴许还低头看了她一眼,但是安言闭着眼睛,所以不知道,只是头顶传来他淡淡的嗓音,“那不是你的家,我看路轻绝应该要回来了,到时候你不搬走都不行。”
男人语气太笃定,安言不禁怀疑地问,“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脚步未停,抱着她上楼梯,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总觉得他今天好像脚步有些虚浮,有好几次她紧紧捁着他的脖子都以为自己要掉下去。
以为她真的很排斥,所以他踩着步子准备往侧卧去,安言像是想到了什么,叫住他,“去主卧。”
他不解,“不是说怕做噩梦?”
安言微微一笑,看着他,“既然我恨你你都能当做一种感情,那我总不能真的一辈子不睡那间卧室,你说呢?”
听到她这么说,萧景皱紧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而是说,“安言,我说了不会勉强你,希望你也可以不用勉强自己。”
女人嘴唇动了动,应该是想说点什么,但是空气中蓦地响起手机的震动声,萧景此刻还抱着她,感受到手机震动,对她说,“手伸到我右边裤袋里,有电话打进来,估计是茯苓。”
安言没动,他也站住没动,近距离看着她纤长的睫毛。
愣了几秒钟,她还是慢慢松了一只手往他的右边裤袋摸去,看也看不见,她胡乱地找着,然后头顶传来笑声,“你往哪儿摸?”
他话音刚落,安言骤然就觉得自己摸到什么硬硬的东西,吓了一跳,下意识以为自己摸到了……
立马就想将手收回来,但是他并没有让她这么做,而是循循善诱道,“伸进去,将它拿出来。”
一不做,二不休,安言直接伸进去一通乱摸,将那块手机拿出来,茯苓两个字停留在手机屏幕上,她还没接,男人直接抱着她朝卧室走去。
一边对她说,“估计是她到了,你接了将密码告诉她。”
安言一边滑开接听键一边说,“难道她身为你的管家,不知道这座房子的密码?”
最终还是她将密码告诉给了茯苓,萧景已经用脚踹开了卧室门,反脚又勾上门,将她放到床上,然后又将她的鞋子给脱了。
安言翻身起来坐在床上,抬头望着他唇上的伤口,那是早上在沙发上被她咬的,“你准备一直都让我住在这里?”
男人绕到床的另外一边,将落地窗微微拉上了一点,露出一道人那么宽的缝隙,然后回到床边,“我倒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我不逼你,我等你自己做决定。”
“……”
“你出去吧,我休息一下。”
她将将背对着他躺下,男人直接走过来,将她的身子赶过来,俯身就吻住她的唇,不带任何侵略性,但是异常火热缠绵的吻。
偶尔她舌尖扫过他唇上的伤口,会引起他轻轻的抽气声,于是她挣不开但为了让他难受一点,故意用唇扫过那个地方——
那人大掌捧着她的脸,给她一种醉醺醺的感觉。
她的恶作剧萧景并没有理会,反而将她吻得更深,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男人的情欲,他率先将她放开,看着自己的杰作,安言的一张红唇微微红肿,眼中带着水意。
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笑,“想让我难受的方法不是这个,安言,你这样并不会难受,或许你的动作可以再大胆一点?”
她气恼,不再理会他,兀自闭上了眼睛,想起放在她摸着他脖子处的热度,很明显比她的体温还要高,淡淡地说,“我劝你还是悠着点儿吧,我觉得你已经被我传染了。”
他似乎很是愉悦,笑了笑,“那正好,两个病人正好待在一起,不用出去见别人。”
安言翻了个身,将被子拉高,毫不犹豫地开口,“你想的美。”
男人又站着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目光有些骤然变得有些复杂,最后还是将她的被子掖好,轻轻地离开了。
安言以为自己睡不着,但是没想到困意来的很快,在她将睡将醒时,放在床头的电话不停地震动,她以为是萧景的电话,所以没管。
但是那持续不断的震动声锲而不舍地响起,安言慢慢打开眼皮,伸手将电话给拿起来,在看到来电显示上的人名她睁大了眼睛,睡意瞬间醒了一大半。
她赶紧接起,竟是有种想哭的感觉,“喂,路警官你终于有音信了。”
路轻绝在那头笑了下,声音带着包容和歉意,低低的,“安言,难不成你还想我这个男朋友了?”
安言抱着被子,眼中闪过戏谑的光芒,很自然地嗯了一身,接着说道,“是啊,早都说过是男友力爆棚的男朋友,昨天我被人欺负了,要是当时你在场的话,我不信谁还敢欺负我。”
“被谁欺负了?”
想起昨晚在酒店的事情,安言笑了笑,“但是欺负我的那人比我更惨,想到这点,我心里平衡了一点。”
“看来你还是赚的,并没有吃亏。安言,我一个星期后就回来了。”
离开了这么久,虽然安言对他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两人总归是朋友,她想了想道,“需要我去接你吗?”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