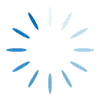女人伸了个懒腰,妩媚地乜他一眼。像是早有预料。
“你是不是跟隔壁邻居——睡了?”
谢泳想起刚刚邻居那得意的眼神,就知道自己头顶又绿得发光了。
“嗯。”
“你说怎么办?”
“我帮你口。”
“好。”
“记住,这是上帝在惩罚你,惩罚你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长长的棒子只是被女人轻轻撸了几下,就硬的发亮,像一杆称悬空在裆部,而那两个巨型卵蛋,像极了红铜做的秤砣。
白粟仰起头,双唇微张,像涂唇膏一样被“这杆秤”一遍遍轻描、抚摸。
一股淡淡的檀香味传来,他一直很爱干净,一天沐浴三次,几乎闻不到尿骚味和臭味。
这样美味的肉棒,可是她吃不到,只能忍耐。
在他不主动进来之前,只能忍耐。
但她同样也知道,忍耐的不止她一个。
“别忍了吧。”
只要往进挤一点点,他的龟头就能接触到她的舌头、牙齿,但他就是要克制,停在门外,徘徊徘徊。
其实,她也并非不知道他不往嘴里插是因为什么——他喜欢折磨自己,拿他的话说是“赎罪”,只是她有点厌恶了。
为什么她和他之间总横着上帝这个第三者。
上帝说,人人都有原罪,要克制你们身上的动物本能,是为了更好的接近上帝,赎清罪过。
上帝说,为了我,男孩们,别做爱,离女人那条蛇远一点。
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
白粟很少能从谢泳那获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做爱,但这并不意味他不需要刺激。
刺激是可耻的,所以他需要她作恶,然后用惩罚的名头来释放他的性欲。
很扭曲吧!
当然这也是白粟慢慢总结出来的。
在交往期间,他不碰她,结婚后,他仍然不碰。
就在白粟以为这人是终身禁欲者,在外偷吃了一次的情况下,他却主动操干了自己。
而现在就等着他克服掉内心的耻感,这样她就可以饱餐一顿,不,是接受“惩罚”了。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