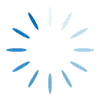傅洵老远就看到那抹被黑裙子包裹着的凹凸有致的身影,不禁挑起一侧眉毛。
直至走到近前才故作讶异道:“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不在豪宅待着,跑到贫民窟找操,向小姐还真是有个性。”
他总是喜欢叫她向小姐,少了几分虚情假意的奉承,更多的是对高高在上的上层社会的一种嘲弄。
他性格一向恶劣。
向绥被他直白的用词闹得脸颊微微发热,但姿态依然高傲,一副屈尊纡贵的模样:“本小姐能赏脸来是你的荣幸。”
她不介意在他面前装腔弄调,拿大小姐的乔。
只是她到底低估了这人的脸皮。
“不巧,我突然想起来家里有事,先回去了,大小姐在这慢慢视察群众生活啊。”
傅洵双手抱胸,闲闲地看着她,压抑着嘴角上扬的弧度,抬腿竟真要走。
向绥心下气恼不已,抓住他飞扬的衣角,扯出很长的一条延伸线。
傅洵低头注视着被扯到快要变形的衣服,无奈往回退了几步,成功解救下可怜的衣服边。
“向小姐是欲求不满吗?”
向绥这回可懒得搭理他,木着一张脸:“少废话,去哪做?”
傅洵讳莫如深地指了指近处的一座房子:“知道这儿是哪吗?”
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熟悉的破墙烂瓦映入眼帘,广告纸的碎片还残余在上面,向绥想不记得都难。
傅洵的家。
但她当然不能说,她只能装作不认识。
向绥不耐烦的用膝盖狠狠顶向他的大腿,并没有回答。
傅洵也没有很想得到答案。
他慢条斯理地伸腿回挡,像制止小猫的抓挠一样轻松阻挡了向绥的攻击。
“是我家。我的父母正在屋里午睡。”
“哦,知道了,所以什么时候做?”
兴许是想到了两人曾经肏干的场面,她的穴痒得厉害,忍不住催促道。
傅洵还是摇摇头,气定神闲地望着她,嘴角依旧挂着令人讨厌的笑容。
“我也要回去午睡了。”
她忽然有些生气。
方才手机上分明是同意的意思,现在这又是在做什么?
她是来宣泄生理欲望的,不是找不痛快的,器大活好的帅哥排着队追求她,不是只有你傅洵一个。
可她为什么还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人,甚至眼巴巴的跑到人家门口摇着尾巴求肏?
这显然不是一时半会能想通的。
就像鱼相伴水更蓝,鹰燕同行山更青,很多事天生如此,没有道理。
察觉到向绥衍生出一些负面情绪,傅洵反而觉得不可思议,这人似乎跟从前相比有哪里不一样了。
有变化就代表变故,变故会导致未来不可掌控,这一点他倒是同向绥一样,都厌恶失控。
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吗?
可他的下体硬得发痛,早在鼻腔嗅闻到女孩柔软的气味之时,早在二人磁场相接之时。
他觉得向绥这人真邪乎,总像个药效强烈的春药似的,把人心底里潜藏的那点淫靡欲望都勾了出来。
她的裙子下面有野兽。
傅洵抓起向绥软若无骨的小手按向自己腿心,炙热的坚硬在触摸下震颤。
向绥忽然又平静了,或许是这人身体上的急不可耐让她明白,占主导地位的从来都不只是某一人,她还有什么可消极的呢?
跟谁计较也不要跟狗计较,傅洵一直是条爱咬人的狗,她倒是先沉不住气了。
看来今天确实是被别墅里那两个人影响了心情,都变得有些不像她了。
熟悉的冷笑又重新挂上她的嘴角,她在短暂的ooc后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葱白的手指捏住傅洵胸前外套的金属拉链,从上往下缓慢拉动,像是逐渐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露出东方伊甸园结出的禁果。
“别在这里。”这次换成傅洵低声警告了。
原来还有你怕的东西?
向绥像是终于抓住他的弱点一般,瞬间耀武扬威起来,她笑的明媚又妖艳。
“是吗?那我偏要。”
指尖抵在他胸膛之上的小肉尖儿处,隔着布料缓缓画圈。
挑逗般的动作使得傅洵呼吸都沉重起来,他黑炭一样的眸子像是被什么点燃了,暗红的温度正在一点一点浮现。
傅洵把她按到墙上,褪下她的外衫一把丢到地上,扯松吊带,连着胸前的内衣一同拉下,任由衣料堆迭至腰腹。
白兔一样圆润饱满的乳弹跳出来,暴露在空气中,渐渐硬成小粒。
傅洵两指夹住嫣红的蓓蕾,拇指指腹按压着扭转,时不时细细揉捏把玩,两下就弄得向绥腰肢似水,手脚软绵,娇喘连连。
向绥不太注重前戏,甚至可以说没有很喜欢,她总觉得生殖器交合前的任何动作都是虚幻的,像五彩斑斓的泡沫,美丽却毫无作用,只有阴茎插入阴道口的那一刻,这场欢爱才真正被落实。
但傅洵总是给她作为床伴应得到的一切,包括做爱前的抚慰。
这跟完全机械的情欲是有所区别的。
也是傅洵让她知道,自己粉嫩的乳头能够那样挺翘,会阴上方的小阴核也能那样酥麻,敏感。
他也只有在床上才那么合她的心意了。
傅洵倏地伸出两臂托住她的腿弯,孔武有力的臂膀将她整个人悬空,稳稳托举。
骤然的举动叫向绥下意识伸出手臂搂住傅洵的脖颈,一双细腿也缠绕上他的腰。
这个姿势让她想到了树袋熊。
树袋熊的一生几乎都在桉树上度过,它们的前肢和爪非常灵活,可以轻松攀爬高大的树木,并且时常或抱或挂在树干上休憩。
她现在就像树袋熊缠绕桉树一样挂靠在傅洵身上,完全依赖另一方的体力了。
不过傅洵依然能轻松地腾出手撩起她的裙摆,拨开内裤布料,中指抵上腿心肉缝。
穴口早已泛滥成灾,手指无需进行过多浸润,很顺利就插进甬道。
紧致的触感让傅洵呼吸微微一滞。
手指被内壁上的小嘴争先恐后地吮吸着,嫩滑湿润的温腔软肉足以令世界上所有男人疯狂。
傅洵也不例外。
他快速抽动着手臂,仿佛要把蜜穴深处捣得软烂出汁才肯罢休。
他抽插得这样快、这样深,叫向绥敏感的肉体如何受得住,只能被挑在欲望的刀尖上,任由汹涌澎湃的快感淹没神智。
“要到了……啊……!”
缠在傅洵身上的细腿止不住的收紧,如玉的脚趾生理性蜷缩,她与傅洵的胸腔贴合得更紧密了,整个人不由得卸了力,更是完全依靠着他站立支撑了。
傅洵就在这时把她的身体往上提了提,肉棒猝不及防挤入尚处于高潮状态的嫩穴。
二人同时舒服一叹。
向绥修长的天鹅颈一瞬间颤抖着仰高,唇瓣不自觉张开,呼出声声难耐的娇吟。
傅洵认真做起爱时话其实不算多,除却偶尔戳刺向绥几句的荤话以外,更多的是完全沉浸在情欲的浪潮里。
龟头细细感受着壁腔肉粒的摩擦,感受着甜腻蜜液不断流淌、迸溅,他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平稳缓慢的刺激了,猛然提臀发力,狠狠肏捣起软穴来。
没有给向绥缓冲适应的时间,肉棒激烈而勇猛地向着深处抽送,力道重而幅度深,叫她震颤不已。
这回比以往任何一次进去的都要深,因为姿势原因,向绥被顶到几乎飞起来,猛烈的皮肉撞击声清脆入耳,混杂着缠绵的水声,更显淫靡。
她深深地吸气,呼气,仿佛此时就都理解了莉莉周所说的一切。
她听见她的身体里刮起一阵强风。
她化作风筝缠绕在傅洵身上,风筝还在颤抖,少女飞了起来。
她刚刚还在放风筝,现在变成了风筝。
她已成功飞翔。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