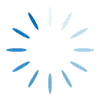此言一出,殿中百官皆是议论纷纷,有真心为惠景侯府、为薛亭晚担心的人,也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
宛氏一个眼刀扫向薛楼月,身后两个膀大腰圆的婆子当即会意,掩于衣袖下的双手死死钳制住薛楼月,冲左右邻桌笑这解释道,“二小姐身子略有不适,老奴扶她先行告退。”
那膀大腰圆的婆子力气奇大无比,薛楼月正欲挣扎,手腕又被婆子大力一扭,一阵彻骨痛意传来,薛楼月登时便疼的噤了声。
那厢,史清婉端坐下首,清丽寡淡的面容上忽青忽白,目光躲闪,眸中满是不安。
方才凉亭之中,史清婉和许飞琼两人正商量这陷害薛亭晚的密谋,不料许飞琼突然被人叫走,许久都没回来。万万没想到,许飞琼竟是被龙禁尉撞破和汪应连在一块!
以前史清婉从未听许飞琼说过对汪应连有意,如今见她突然要嫁给汪应连,便猜到两人之间定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丑事。
方才凉亭之中,两人一番密谋,史清婉被许飞琼的一席话激的怒意上头,见许飞琼许久未归,便派人去找了名身强力壮的小厮,又派自己的心腹丫鬟前去拦下准备回致爽殿中的薛亭晚。
这一切皆是按照她和许飞琼谋划好的计策行事,可以说是□□无缝,如果不出意外,此时,薛亭晚正和那身强力壮的小厮鸳鸯交颈,丑态毕现……
殿中众人正各怀鬼胎,却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紧接着,一声清亮如莺啼的声音从殿外传来,“本县主在此。”
殿中众人纷纷回首,只见丫鬟入画正搀着薛亭晚进殿而来。
她生的极美——远山眉,含波眼,樱唇琼鼻芙蓉面。红酥手,天鹅颈,柳腰莲步轻轻转。
美人儿行走之间,海棠红的裙摆随风飘动,宛如烟云傍身,似有流光在侧,真真是明艳照人,恍若神妃。
只见薛亭晚缓缓抬眸,抚了抚鬓间的多宝鸾凤金钗,“不知许小姐何事相寻?”
那厢,许飞琼正一脸得意,等着献庆帝派人前去撞破薛亭晚和小厮的苟且之事,不料薛亭晚竟是施施然地进殿而来,周身风华无两,压根不像是失了清白的模样!
许飞琼双目猩红,登时挣脱了许父,尖声叫到,“不可能!薛亭晚,你怎么在这儿?!”
薛亭晚提裙行至九龙御座之前,居高临下地垂眸看着地上发丝凌乱,形容癫狂的许飞琼,冷声道,“哦?那许小姐倒是说说,本县主不在这儿,应该在哪儿?”
惠景候和宛氏正火急火燎,叫人去寻薛亭晚,此时见薛亭晚全须全尾、神色如常地进了殿,心中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两颗心才放回了肚子里。
许飞琼被薛亭晚质问的无话可说,忙躲了她对视的目光,一脸惊惧之色再难掩饰。
下首,史清婉见薛亭晚进殿而来,便知道奸计失败,眼见二人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情就要败露,史清婉面色惨白如金纸,心中惊惶不定,一抬手的功夫,竟是打翻了桌上的一尊金盏,将盏中清酒撒了半桌。
史夫人见状,当即抬手叫了宫婢来收拾,皱眉道,“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
史清婉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掩下面上的的不安和惊恐,只兀自垂首,安分的如同鹌鹑。
致爽殿中,众人望着九龙御座前的数人,皆是一脸云里雾里,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正窃窃私语之际,一袭月白色锦袍的裴勍施施然进了殿,身后跟着走进来,乃是御前龙禁尉统领苏易简。
只见苏易简一挥手,立刻有龙禁尉将一名身强力壮的小厮和一名婢女押进殿来,俯跪在献庆帝御座之前。
原来,因今日裴勍邀薛亭晚于梦隐湖泛舟,不愿叫他人撞见,便派了裴国公府的亲卫镇守湖畔,严禁闲人接近。
好巧不巧,严守湖畔亲卫们刚好撞见一小厮和一婢女从湖畔经过,且形迹可疑,亲卫将二人捉拿盘问之后,这才发现了史清婉和许飞琼意欲陷害薛亭晚的毒计。
于是,裴勍与薛亭晚在湖畔分别之后,亲卫便立刻将此事上报了裴勍。
裴勍听了这番歹毒计谋,登时盛怒不已——那是他放在心尖尖上、视若珍宝的人,若是有人蓄意谋害,他裴勍定会诛之而后快,让她们百倍偿还。
于是,裴勍当即下令,派人将薛亭晚引入偏殿好生保护起来,又叫将此婢女小厮二人交送龙禁尉统领苏易简手中,使出这一出“将计就计”之策。
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许飞琼还未来得及加害薛亭晚,便已经入了汪应连设下的圈套中。
史清婉见到那心腹婢女和身强力壮的小厮,登时吓得惊恐万分,两片红唇不住地哆嗦,再也绷不住周身仪态,
史夫人见史清婉今日十分反常,正欲询问,却听那殿上的白衣上卿朗声道,“臣有事启奏。方才,臣在乐游苑中撞破了一桩蛇蝎诡计,特地擒拿了走狗爪牙上殿,还请皇上为躲在背后指使此二人的歹人定罪。”
献庆帝一听,面带诧异道,“是何蛇蝎诡计?”
苏易简冷冷盯了眼俯跪着的小厮和婢子,斥道,“皇上御前问话,还不速速招来!”
那小厮和婢子被龙禁尉扭送到致爽殿中,已是吓得双腿软绵,语不成声。此时见献庆帝天颜在侧,又想起自家主子交代的毒计,不由得心神俱灭,胆颤不已,竟是一股脑儿把史清婉和许飞琼指使他们陷害薛亭晚的事情交代了个一清二楚。
薛亭晚婷婷立于一侧,听着那小厮和婢女的交代,心中若说不气不怒是不可能的。
上回,许飞琼害薛亭晚受伤,许父拿藤条毒打许飞琼,惠景候和宛氏可怜许飞琼被亲生父母如此苛待,心存仁念放了她一马,没想到,许飞琼不禁不感怀恩情,竟然还以怨报德,生出如此毒计加害于她!
同为女子,却想出毁人清白这样阴险歹毒的计谋,何其心狠手辣!
只见薛亭晚杏眸中泪意盈盈,莹白的小脸儿上滑下两行泪水,提裙跪向献庆帝,梨花带雨地娇声泣道,“臣女平日里和许小姐,史小姐井水不犯河水,如今,却被人用如此下作卑鄙的计谋陷害!若不是裴大人和苏统领相助,臣女险些,险些就……臣女求皇舅舅做主!严惩背后主使之人!”
薛亭晚是什么人?是惠景侯府的嫡长女,是皇太后跟前的开心果儿,是论辈分该叫献庆帝一声“皇表舅”的人!
献庆帝听闻了此事的始末,也是龙颜大怒,又见薛亭晚一口一个皇舅舅这般梨花带雨的可怜模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登时便将手中金盏砸向了史氏一族的宴桌,怒喝道,“带罪女史清婉上前!”
那厢,惠景候听了那小厮和丫鬟的招认,登时便暴怒而起,两三步到史氏宴桌前,揪着史太傅的衣领,抬手就朝史太傅脸上抡了两拳。
顿时,席上一片尖叫,有两三个官员壮着胆子上前拉架,却被惠景候一脚踹开,只见他边打,边怒骂道,“你这老贼平日里人模狗样,教养出来的女儿却恶毒至极!我呸!你们史家愧对帝师之名!愧对本候的宝贝女儿!”
史清婉躲在史太傅身后,整个人哆哆嗦嗦,身子软的坐都坐不住,几欲滑到在地。
两名小黄门肃着脸上前,一左一右,将史清婉搀扶着押上了殿前。
史清婉扑在地上,不敢看身侧的薛亭晚,更不敢看身侧的裴勍,电光石火之极,忙大声哭嚎道,“不是我,不是我!此事全都是许飞琼一人的计谋!全都是她的计谋!”
那厢,许飞琼见大势已去,正欲神不知鬼不觉地退下,不料史清婉竟是临阵倒戈,将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许飞琼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故作平静道,“史姐姐何出此言?这身强力壮的小厮,是史府家养的,这婢子,也是史姐姐贴身伺候,史姐姐就算血口喷人,也要拿出些证据来才是。”
那厢,汪应连听了二人的你一言我一语,心下不禁狐疑许飞琼是否真的参与了陷害史清婉之事。
但转念一想,如今他和许氏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许飞琼若是卷入此事,对他汪应连的仕途可是半分好处都没有。
思及此,汪应连忙笑着开口,为许飞琼开脱道,“方才飞琼一直和臣呆在一块,我二人寸步不离,飞琼又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中去?再者,飞琼性情温顺,平日里连兔子肉都不敢吃,这等狠毒的计谋绝不会是她想出来的。”
史清婉闻言,心如死灰,万念俱灭,只见她发丝凌乱,形容枯槁,面上泪痕皆干,不住摇头道,“你们说谎,你们说谎!”
御前大太监一甩拂尘,呵斥道,“大胆!御前哪是你这罪女喧哗之地!”
那厢,裴勍知道献庆帝赐婚汪应连和许飞琼的圣旨已下,自然明白此番汪应连是要全力保下许飞琼的。今日陷害薛亭晚之事,乃是史清婉全权操作,眼下若要治罪,也只能治一个史清婉了。
至于剩下的许飞琼……此女心术不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究是好过不到哪里去的。区区一个汪应连又能庇佑她多久?
总之,以后有他护着薛亭晚,再也不会叫这些魑魅魍魉近她的身!
裴勍和苏易简相视一眼,拱手道,“此事已水落石出,请皇上治歹人之罪。”
那厢,史太傅和史夫人老泪纵横,奈何人证物证俱在,腆不下老脸去献庆帝前求情,只哭求地看着皇后,希望皇后能在献庆帝面前为史清婉求情几句。
之前,皇后确实有意指史清婉做太子妃,借助史氏一族在文官中的声望,助太子安安稳稳地登上大宝之位,如今见史清婉已经身败名裂,自然也打消了和史氏结亲的念头,只见皇后只低头饮着茶水,垂眸避开了史氏求助的目光。
殿内,百官交头接耳,有主张处死史清婉的,有主张法外开恩的,更有和稀泥,主张史氏和惠景侯府两家私下和解的。
只听一文官道,“这史家号称帝师之家,出了数位太子太傅,若是今日严惩了这史小姐,岂不是将他家的历代清名毁于一旦,叫天下文人怎么看呐?!”
御座一侧,德平公主本听了史清婉意欲对薛亭晚做的事儿,本就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此时闻言,当即冷声道,“皇子犯法与庶人同罪!史小姐只是区区臣子之女,怎么就罚不得了!?”
说罢,德平又看向献庆帝,语带哭腔,“父皇!此番决不能饶了这等蛇蝎女子,父皇定要严惩其罪,给天下人做个公正为民的表率!”
那厢,皇太后听了这狠毒计谋,亦是气不打一处来,老嬷嬷上前顺了好久的气儿,皇太后才勉强缓过来,指着史清婉道,“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心思便如此恶毒!竟然想着陷害我们阿晚的清白!哀家倒要看看,你们史家是不是把整个皇族,所有姓薛的都不放在眼里了!”
惠景候、宛氏、薛桥辰上前,亦是冷然道,“事已至此,惠景侯府阖府上下不求任何补偿,只求严惩史氏之女的罪过,望皇上明鉴!”
史夫人哭嚎着上前,史太傅不住地磕头道,“求皇上开恩!老臣回去定会好生管教女儿,求皇上开恩呐!”
宛氏闻言,怒骂道,“你个言而无信的老东西!上回你女儿构陷我女儿的脂粉铺子,连累怀敏郡主烂了脸,我想着给你留三分薄面,让你自己管教,不料竟是放虎归山,大错特错!如今你那歹毒女儿接二连三做下这种卑鄙下流之事,你竟还有脸求情?!”
史太傅被宛氏骂的没脸没皮,奈何史清婉是他的亲生女儿,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真真是怒从心生,悲从中来。
“史氏之女史清婉,阴险歹毒,蛇蝎心肠,意图毒害宗室之女,犯下不可饶恕之罪。朕心痛至极。现将其打入天牢,施烙刑,钦此。”
太监宣旨的声音刚落,龙禁尉便应声上前,拨开抱着史清婉大哭不止的史夫人,将史清婉拖了出去,史太傅见状,亦是两眼一翻,当场昏厥了过去。
九龙御座上,献庆帝望着这一场闹剧落下帷幕,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史氏一族乃是文官中的流砥柱,如今史清婉做下这等罪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打入大牢,已经算是轻微的处罚了。
献庆帝挥了挥手,立刻有宫人上前,将嚎啕大哭的史夫人和不省人事的史太傅扶了下去。
那厢,薛亭晚还脊背挺直地跪在地上,见史清婉恶有恶报,自食其果,心中并无过分喜悦,倒是颇觉酸涩难言。
这么凝神感慨了片刻,薛亭晚才发觉膝盖跪的有些发麻了,正欲起身,不料面前竟是伸过来了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掌。
薛亭晚抬眸一看,正对上裴勍那张俊逸出尘的玉面。
他将修长的手往前送了送,嗓音清润低沉,让人莫名心安,“臣,扶县主起来。”
☆、第50章年关将至
望着男人深若幽潭的双眸, 薛亭晚鼻子一酸, 就想扑到那个结实的怀抱里。
可当着殿中众人的面儿, 不能暴露两人的关系,薛亭晚心中情丝再缱绻,终究存了几分理智,伸了柔弱无骨的小手儿, 扶着男人的大掌缓缓起了身。
殿中风波乍平, 众人一阵唏嘘感慨过后,该喝酒的喝酒, 该吃菜的吃菜。
此番有惊无险, 宛氏上前抱着薛亭晚一阵痛哭, 惠景候更是连声感谢裴勍的出手相救,非要拉着薛亭晚给裴勍行一个谢礼。
裴勍推辞不过, 侧身受了薛亭晚一礼,只得又给惠景候和宛氏恭恭敬敬回了个晚辈礼。
那厢,薛亭晚桃腮微红,刚落座于席间, 便被德平公主抱了个满怀。
“我无事的, 你瞧,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薛亭晚安慰了德平一番,望着她因担心过度而泛红的双眼,略想了下, 轻启樱唇道, “有件事情……我想要告诉殿下。”
薛亭晚和德平是做了十来年的闺中密友, 如今,她和裴勍在一起的事情虽要瞒着众人,但却是不想瞒着德平的。
见薛亭晚毫发未伤,史清婉被下大狱,德平心中痛快不已,松开薛亭晚,笑道,“你说,我洗耳恭听。”
薛亭晚倾身过去,低声耳语了一番。
德平公主听了这番话,略挑了秀眉,将手中金樽和薛亭晚的金樽碰了碰,笑的颇有深意,“那本宫就祝你们二人终成眷属。”
薛亭晚见她面上只见喜色不见惊讶,纳闷儿道,“你怎么一点都不吃惊?那日,裴勍同我表明心意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呢!”
德平公主饮了口金盏中的桂花酒,笑道,“因为本宫早就猜到了。先前女学之中,一惯冷漠的裴大人待永嘉县主举止亲密,种种反常。后来端午宴上,裴大人又亲自抱着永嘉县主去裴国公府疗伤。起初我只是略有怀疑裴勍对你有意,可方才在殿上,本宫见裴勍为了帮永嘉县主讨回公道,甚至不惜和史氏一族结仇。心中便也有了确切的答案。”
说罢,德平公主面上绽开一抹促狭笑意,“刚刚你哭的梨花带雨,泪眼朦胧,定是没看见裴勍凌厉逼人的样子——他脸色阴阴沉沉,周身气场骇人,那架势,几乎要把史氏一族生吃活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史氏怎么招惹他了呢!”
薛亭晚听着这打趣的话,小脸儿上红的不成样子,“你你和苏易简都是成了精的!我这个戏中人,竟成了被蒙在鼓里的了!”
德平公主面上笑意渐渐淡了,正色道,“阿晚,裴勍对你用情至深,就连细枝末节也无微不至。”
“这些明晃晃的情意,并非是你察觉不到,而是裴勍有意百般呵护着你——他想叫你做个不识愁苦的稚子。”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德平公主几句话,如醍醐灌顶,将薛亭晚点了个通透。
</div>
</div>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