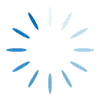第二天Y带她去医院,医生应该是他的人,给她检查身体时皱起眉。
“有点撕裂,”她摘了手套,转头对帘子外的Y说,“你怎么回事?把人弄成这样?”
Y说:“她昨天吃了避孕药,给她做个检查。”
医生叹了口气,掀开帘子对Y说:“你给我出去。”
Y没说什么,走出门后,医生小声对Z说:“如果你有顾虑的话,我可以帮你跟他的父母说这件事。”
Z心下一暖,却说:“谢谢你,不用了,我会自己处理的。”
“况且,”她的语气转凉,提高音量,仿佛故意让外边的人听见,“这应该也不是他第一次干出这种事了吧?”
医生的表情却怪异;“不是,之前从来没这种情况。”
Z沉默,检查完后她走出房间,Y站在外面,看了她一眼,对医生说,给她打皮埋避孕。
医生怔了怔:“你确定?”
她的目光转向Z,像是要征得她的同意。Z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着Y说道:
“这么迫不及待吗,Y先生?”
Y盯着她:“他们必然会在不久后催我们生孩子,想方设法知道我们有没有避孕。你想这么早就怀孕吗,Z小姐?”
他俯下身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就算你不做,我照样内射你。”
Z的后背紧绷,呼吸乱了几分。
她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冷淡地说道:“打吧。”
她躺在在手术床上,等着护士给她的手臂消毒,做局麻。她早上起来没有化妆,眼皮倦怠地垂着,透过白皙的皮肤能看见红血丝,眼睛下有淡淡的黑眼圈。长发像瀑布一样垂下,整个人笼罩在早晨的光晕中。
医生在她的手臂上切开一个小口,将植入器推进皮下。切开皮肤的时候,她的身体缩了缩,另一边手指蜷进手心。
皮埋做好后,医生在伤口处包扎,让她坐着休息。她抱着手臂坐在外面的座椅上,Y全程看着,站在她面前。
无言。
Y开口道:你在做的收购虽然目前比较顺利,但是竞争对手也不弱,要想成功拿下,先要解决掉他们。
Z抬眼看他:“Y先生有何指教?”
“有一个项目在找合作方,”Y说,“正好是其中一个的竞争对手,我向他们推荐了你。”
Z说:“早知道做皮埋还能跟Y总换项目,我就多打几个植入器了。”
Y听到这句话,目光从报告上移过来,沉下脸。
“你把手臂打穿了也没用。”他说。
Z盯着他看,叫住了路过的医生,说道:“给他做个体检。”
“可是他刚做过。”医生说道。
“再做一个。”Z温和地说道。
察觉到Y正眼神阴沉地看着她,Z神色不改,接着说道:“我怕脏了。”
医生给Y工作多年,就连她听了也心惊胆战。其实这些人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定期做体检的,Z也看过Y之前的体检报告。
她坚持要这样做。Y看了她一会,医生差点以为他要发火,但他却笑了,让医生去准备。
“放心,我是干净的。”他说。
Z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好了吗?我不会逼迫你接受我的提议,既然你不像当初表现的那么愿意,我答应的事情不会违背。”他说。
她愣了一下,又想到昨天发生的事,哼了一声:“真的吗?那昨天那个女人跪在你面前,难道只是为了给你看手相?”
“这是逢场作戏而已,”他笑得弯起眼睛,俯下身靠近她,“我就不信你在跟富婆谈生意的时候,没有点过男模。”
Z不出声了,他却眯起眼睛:“你真点过?”
Z小声说:“神经。”扭过头不想看他。
他抓住她的手腕,强迫她不能动。她“嘶”了一声,挣扎道:“你弄疼我了!”
他说:“注射皮埋的不是这边。”
“昨天你弄的,”她眼眶开始红了,“你抓得我好痛。”
他松开手,看她揉着被他抓过的手腕,嘴里嘟囔着什么,像是在骂他。
“你当时怎么不说?”他皱着眉问。
“我说了有用吗!”她瞪着他。
“有用的。”他说了一句。
他们忽然沉默着不说话,这时医生过来叫他去体检,他才转身要走。
走之前他想起了什么,转头对Z说:“最近你要搬来和我住,就明天吧,我派人去你家。”
Z:“?”
“这是我们两方家长的意见,”他对她温柔地笑,满意看到她绝望的神情,“希望以后相处愉快,未婚妻。”
Y没有骗人,她也收到了通知。不过她拖延了一个星期,直到被双方下了最后通牒,才不情不愿地搬了过去。
她提出了各种要求——分房睡,要一间工作用的房间,给光明单独一个房间(“因为它是只内向的小狗。”),每个房间的温度和湿度要控制成不同的范围,因为这会影响她在不同状态下的心情,等等。
这些要求他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这令她觉得无趣,后悔没再多提一些真正离谱的要求。他们像两头离群独居但不得不住在一起的狼,在这个豪华领地的两端相互试探,但真正推动的却隐身在后,欣慰地观看一对男女走向安排好的婚姻。
他们在这段时间里还算相安无事。两个人的时间表不一致,经常出差,有时也不在这过夜,就算同时在家,也是各忙各的事情。当他们的助理在同一个住所里相遇时,表面上礼貌寒暄,实则心中十分复杂。
这是夏季的末尾,天气却无比炎热,苟延残喘的气温反扑,似乎要给世界最后一击。
Y走进门,在玄关松开领带。他走进屋子,室内只开了方便经过的壁灯。他的目光扫向落地窗边,忽然停下来。
落地窗边的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几乎隐藏在皮质沙发的阴影里,如果没有仔细看,很可能就忽略掉。他走向窗边,脚步轻缓。
女孩的一只手搭在扶手,手指贴着玻璃,留下白色的指印,窗外的光隐约落在她的脸上,露出半张妆容精致的脸。她闭着眼睛,细长的眼线有些晕开,像是萎靡的藤蔓,在素净的脸上居然显出些许艳丽。
她以一种别扭的姿势缩在沙发里,呼吸起伏,看样子是睡着了。他走近她,发现她穿着一件白色套装,从头至脚流畅的线条,复古的垫肩和深V。她大概是考虑到场合,领口用一颗蛇形胸针扣起来,现在已经解开了,挂在一边的领子上。V领在这个姿势下有些许凌乱,微微向旁垂,露出沾着汗珠的胸口和锁骨。
这让他想起年少时看过的一幅画,叫做《水中的奥菲丽亚》,作者是一位德国画家。他觉得很奇怪,即便世界上存在众多有沉睡少女元素的油画,当他看到她时,他的脑海中第一时间冒出的却是这个。
或许听过她的姓名。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人们对她的印象如那些着名的画作所表现的那样,浪漫而凄美的溺亡。对她的美丽的赞美和凋零的歌颂,由此的联想卧在沙发上的女孩的情态,不可多见的宁静。
他曾经也是观赏她的观众,甚至可以说在看到她的一刹那,他才发觉自己陷入迷恋。
可是当站在睡着的女孩身前时,他心中却觉得不详,宛如远处回荡的一道刺耳的钟鸣。
目睹恋人刺杀父亲而精神失常,失足跌进河里的奥菲丽亚,伴着漂浮在水上的睡莲,点缀她纯真的容颜。
她是男人间争斗的受害者,实际上在水中停留不久,就沉入水下的泥沙中。然而她成为了从古至今画作美的死亡的对象,为她举行一场又一场盛大凄美的葬礼,被凝视、被想象、被观赏。来来往往、灯光下影影绰绰的人群凝视她……画面变换,直到在这个落地窗边,他凝视着她。
你们为什么要注视?
他忽然感到一丝恐慌,弯下腰探她的鼻息,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然后手触摸她的脸颊。指腹轻轻触碰,他感觉到她的脸上浮着一层冷汗。
“醒醒。”他抓住她的肩膀。她睡得并不深,被他叫醒,睁开眼睛。
她的眉头皱着,脸色并不太好,嘴唇动了动,声音微弱:“我在这睡着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的?”他问,看到她摇了摇头,又问,“不舒服?”
她的手心也出着汗,皮肤冰凉。她动了动嘴,说:“我来例假了。”
他怔了怔,问道:“疼?要吃药吗?”
她摇头,说:“不疼,但就是小腹坠……而且头很昏。”
她的神色倦怠,于是他没有再多问,抱着她起身,说:“去床上休息。”
她在昏暗中的眼神恍惚,穿过走廊不知不觉间进了她的卧室。他把她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她抓着被角,看到他掀开被子坐在床的一角,往后缩了缩。他居然伸手要去脱她的衣服。
她气得声音颤抖:“都这时候了,你还想要……”
“……想要什么?”他的手一顿,看着她的表情,很快就明白她的想法,失笑,“我在你眼中就那么禽兽?”
他说,他是要给她换衣服,她已经出了汗,穿着这件衣服会难受。她半信半疑地听从了,抬手配合他脱掉。她埋在被子底下带汗的胸口白皙晶莹,触到他的目光,她避开视线,拢了拢被子。他神色如常,目光移开,隔着被子将她剥光,起身去她的衣柜拿睡衣。
这时候她赶忙说能自己穿上,他站在床前,看她躲在被子里窸窸窣窣地摸索,最后露出一个脑袋,说已经穿好了。她的脸色依然苍白,躺在床上,听到他出去打了个电话。
她的意识飘荡在脑海里,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到身后有动静。床的一侧被子掀开,另一端一沉,他躺了进来。
他的身体靠近,她感受到来自他的温度。一只手从她腰后绕过,隔着衣服覆在她的小腹上,温热感传来。
“这是什么?”她小声问道。
“暖宝宝。”他在她耳边说,“觉得烫就告诉我。”
过了一会,她说烫。他撤走暖贴,手伸进衣服贴在她的小腹上。她浑身别扭,在他怀里动了动,被他制止,说这样才没那么难受。
她安静下来,皮肤和干燥温暖的手心触碰,苦艾气味随着她的呼吸愈发明显,好像她整个人都蜷缩在这只手掌下。
“睡吧。”他说道。
她睡了有好一会,头昏脑胀的,说不想再睡。清醒又恍惚地睁着眼,看见窗外的光透进来。
于是他说,那就说会话。
说什么呢?当两个人平和地共处一室时,又不知道对话该怎么进行下去了。
她想了想,说:“那我们来互相问问题,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必须要回答。”
他挑了挑眉:“好。”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