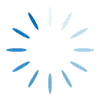谢景行手上一空,看向孟冠白,眼里毫无波澜,“说就说,怎么还抢我的书?”
几年的朋友,他早已习惯孟冠白的不按常理出牌。
孟冠白将手中的书合上,又将其卷起来敲在手心,“那定是与你有关,我才会如此。”
谢景行这下是真的惊讶了,眼里疑惑顿现,“与我有关?”
不只是他,其他几人也都看了过来。
孟冠白卖够了关子,这才说道:“据盛大家弟子传出的消息,盛大家之所以会来通州府学,是听闻府学辩论之风盛行,盛大家一生来往多地,几乎跑遍了整个大炎朝,倒还是第一次听说‘辩论’,想来见识见识。”
被卷成筒状的书猛地直直指向谢景行的鼻尖,“这辩论不正是由你首倡的吗?不与你有关,还能与谁有关?”
伸手抽出那本书,谢景行将其展开,又顺平书页上的皱褶,他想起来了,其实在华夏古代书院也常进行会讲活动,形式还更加多样,有升堂讲说,还有学术会讲等等。
而大炎朝的会讲活动形式单一,一般只是由经学大家阐明自己的经学见解,并不像华夏古时那样还会有不同的观点碰撞,有时甚至还会进行论辩交流。
他还未曾说话,孟冠白就已喜不自胜地猛拍他的肩膀,大笑道:“此次也是多亏谢兄了,我才能得见盛大家真容,有幸能聆听他的教诲。”
就连少言寡语的萧南寻和寇准规也对他拱手揖了一礼,以示多谢。
看来这盛大家确实颇得读书人尊崇,不然大家不会如此反应。
谢景行以为他与此次会讲活动的牵扯只限于此,可没想到,转过三日后,课室夫子将他从课室里唤出去,说是山长有事找他。
他一头雾水地去了山长室。
这是他第二次来山长室,上次还是屿哥儿从屋顶掉下来后,他们被叫来这里受训。
他进山长室时,早已有其他几位学子在此,都是脸熟的人,甚至还有同一课室的同窗,寇准规和萧南寻、吕高轩也在此。
谢景行进去后,便同其他几人等在一处,之后又陆陆续续来了两人,丘逸晨最后进来。
一共十人。
谢景行环视一圈,他们六人中,除了孟冠白全部在此,也不知山长所为何事?
他们五人很是自然地站着,同其他人一般,并没有说话,等山长过来,事情就见分晓了。
他们等了一盏茶的功夫,山长就走了进来。
也没让他们多加猜测,山长直接说明了找他们的来意,“五日后就是盛大家来府学举行会讲的日子。”
山长语气严肃,“府学还是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的会讲活动,事事都需要精心,这时叫你们前来,倒不是让你们负责场地一类的杂事,只是到时安平省八府的官学和私学都会有代表前来,你们十人皆是府学里出类拔萃之人,万一有客人要与府学学子比斗,你们还得尽心。”
他以往也去其他地方参与过类似的盛会,自然知道这么多的读书人聚于一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谢景行当即会意,这是让他们作为通州府学的门面,展现府学的实力,说不定还有着让他们力压群雄,将通州府学之名发扬光大的意图。
不止他懂了,其他几人也都心神领会,纷纷低头恭敬应是。
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体里都有颗好胜的心,谁又会愿意被旁人认为学识低人一等呢?
既然这次盛大家将会讲活动地点定于通州府学,他们也该趁着这次机会,展示一番通州府读书人的实力。
没见通州府学盛行的辩论连盛大家都好奇,足以证明通州府府学可一点也不比其他地方差。
被寄予了厚望,十人陆续从山长室里出来,谢景行还没走出山长的院子,走在他后面一位学子就将他叫住了。
“谢兄。”
谢景行应声回头,叫住他的人是与他同在甲三班的杜留良,“杜兄。”
杜留良大步赶上,走到他身边,两人并肩往外走,他的身高不矮,不过走在谢景行身边时,却显得他气弱不少,原因在于他身体过于瘦削。
同窗两年有余,谢景行也知他这位同窗就是典型的读书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心只读圣贤书,每次月末文考都能排在府学前列,可骑射课就只能勉强不垫底了。
等出了院长所在的院子,杜留良才道:“山长既然选了你我十人出来,到时还望我们十人能守望相助。”
丘逸晨与吕高轩在后面对视一眼,虽然不明就理,却仍然点头,谢景行更是直接道:“这是应当的,同为府学学子,自然该互帮互助。”
杜留良得了大家的应承,才仿佛放下了心,松一口气,对着谢景行点点头,笑着离开了。
等他背影消失在阶梯转角,丘逸晨才奇怪问道:“我没记错的话,这位杜兄文采过人,每次月末文考都能排在府学前五,不该如此担心吧,居然还特意叫住我们言说此事。”
谢景行帮他解了惑,“他自是不用担心与人比文的,不过其他府的学子千里迢迢赶过来,难道就只会与我们论文?定也会在骑射等方面与我们一较高下。”
丘逸晨当即明白过来,骑射他不用担心,不过,他脸上勾起坏笑,过去谢景行身旁,调侃道:“骑马谢兄当然没问题,不过若是射箭,恐怕杜兄是求错人了。”
谢景行面不改色,来了府学四年有余,他的射箭仍然是整个府学垫底的存在。
教授他们骑射课的教官已经换了三个,可任谁见到他,都只能摇头叹气,那些文人常说的“孺子不可教也”是什么意思,在谢景行身上,他们是彻底体会到了。
谢景行在府学可以说是闻名遐迩,除了记笔记、辩论以及马球打得好之外,还有就是文考排名已经连续两年高居榜首了,再无任何一人能将他挤下首座。
连谢景行文考时所写的文章,他们都已经背了不止一篇。
可更让府学学子津津乐道的,是他糟糕的数年如一日的射箭技术。
谢景行无比坦然地说:“这不是还有你们吗?他也不是对我一人说的,只是唯独与我相识罢了。”
丘逸晨很是促狭,兴致勃勃地问:“若是真有人与你比试射箭,你该如何?”
谢景行一点不慌,“日后的事,日后再说,还是莫‘齐’人忧天了。”他直直地盯着丘逸晨,脸上似笑非笑。
丘逸晨好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齐”非“杞”,气得笑出声,谁忧了?反正真有那一日,丢脸的也不是他。
四日间,由安平省其他府城来的读书人就陆陆续续到了通州府,盛大家也早就到了。
不过盛大家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根本轮不到府学的学子出面,山长和府学的教官早已为其安排好了食宿。
通州府学面积不小,几乎占了大半边山的地界,虽然在通州府学读书的学子也算多,不过另收拾出来几间院落供远道而来的客人居住,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几日间,府学里学子读书的心思都淡了,一门心思期待着盛大家的会讲。
许是为了一炮打响通州府学的名声,山长对此次会讲活动极其上心,连食宿安排都会去亲自监督,据丘逸晨说,他这四日已经在斋社里撞见山长不止一次了,首次时,还以为他又犯了什么错被山长逮着了,结果发现山长只是去看收拾出来的斋舍如何?
说到这个,这四日斋舍里也很是热闹,以往斋舍里只有通州府学的学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平日里回斋舍就只是睡觉安歇。
可现在来自四面八方府城的学子的到来,让斋舍热闹得沸反盈天。
被山长打过招呼的十个人,住在府学外的学子还好,如丘逸晨这种白日夜间都在府学的,已是同来府学其他地方的学子斗过诗拼过文了。
若不是场地限制,怕是还得来几场祭祀舞斗。
孟冠白只是听丘逸晨和吕高轩所说就饶有兴趣,可惜他不住在府学里,也没被山长打过招呼,很是哀怨。
这日,谢景行和屿哥儿走进府学大门时,已经连续四日在大门旁见到站成两排,每排五人的勤学工学子了。
他们是负责引导往来府学的读书人的,需要为他们引路,并且介绍通州府学。
到此时,屿哥儿已经完全看不出那一夜莫名的情绪起伏,笑眯眯地同谢景行告别,脚步轻快地进了文清苑。
边疆已经稳定的消息传过来时,最高兴的就是他了,最起码这表示他的二哥暂时是安全的。
谢景行摇摇头,这时离开得倒是干脆。
他转身欲往班级行去,可大门外却传来了一行人的声音,“这里便是通州府学了?”语气听着让人觉着有些莫名,“倒也还算大,勉强及得上我们清河府学的一半了。”
谢景行只觉得他的话听来有些阴阳怪气,站定往后看去,站在大门外的是一行约八、九人的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脸蓄长须,身着青袍的中年汉子。
后面一行人俱是穿着相同制式的蓝色衣衫,有两人与最前面的中年汉子站得甚近,说话的是左侧那个摇着扇子,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的青年人。
他脸上似笑非笑,配着他刚才的话,很明显对他现在看到的通州府学很是不屑。
府学大门处负责接引他们的几名学子脸带怒意,不过因他们是主人,倒是克制住没有说些什么,但却也没有同之前一样直接过去。
谢景行回首看过去时,那说话的青年人还挑衅似地对他笑了笑,不过谢景行的注意力却并没被他吸引住,看他只是一扫而过,一点多余的眼神都没落在他身上。
倒是出声学子旁边的另一位同样年纪的青年人,光是站在那里存在感就极强,让人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莫名其妙的,谢景行居然与那位学子对上了视线,谢景行作为府学学子,他当先同对方颔首示意,那位学子同样回以颔首。
他们这里不动声色的打了个招呼,那边为首的中年汉子总算出了声,“赵朝贵,莫要胡言。”
赵朝贵垂下头,“是,葛夫子。”
可等他抬起头时,脸上莫名的笑意仍在,谢景行心里一哂,这个赵朝贵要么是个刺头,不服从葛夫子的管教,要么两人便是故意的。
谢景行眸色未动,哪里都有这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也不是第一次见。
府学大门处的那几位学子自然也发现了,脸上怒意更深,他们是通州府学的学子,自然以通州府学为荣,当然不会愿意这不知从哪来的人平白无故地贬低府学。
本该上前接引几人进入斋舍先行安顿,这时却迟迟不动。
眼见着葛夫子脸上神色开始变化,谢景行暗叹口气,既然遇上了,他便帮着跑一趟吧。
他转过身,几步走去了府学大门,先是停在了一位眼熟的同窗身旁,道:“严兄,我恰巧要去斋舍寻丘逸晨,这几位客人就由我顺路送去里面吧。”
严学子敛去脸上的怒意,道:“多谢谢兄。”这等无礼之人,他属实不愿同他们一道。
谢景行接着才走去葛夫子身边,拱手一揖道:“远来是客,不知诸位是来自哪里?”就当完全没听到赵朝贵的话一般。
苟夫子道:“我们是清河府学的教官和学子。”
谢景行淡淡道:“原来是清河府学的,久仰。”话说得好听,可面上的神情却很是平淡,显然是客气话,“这几日来府学的客人太多,我许是忙昏头了,竟不知清河府学的诸位应安排在哪里,还请诸位见谅先同我进斋舍吧,那里有专人负责,就是再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都记得,定会将几位安排好的。”语气不卑不亢,像是完全不知他们清河府学的威名。
说完不等回话,便向前伸出左手,恭迎他们入内,不就是阴阳怪气吗?当谁不会似的。
府学的学子们勉强才抑制住嘴角的笑意,忙低下头,不愧是谢景行。
这下轮到赵朝贵脸上升起愤怒了,他就不信这名学子不曾听说过清河府学的厉害。
要知道三年一次的乡试可都是在安平省省府明州府举行,全省学子汇聚一地,怎会不了解安平省每次乡试录取百名左右的举人,几乎三分之一的名额由清河府学和清河府其他学院的学子包揽,又有几乎四分之一由安平省省会明州府瓜分,其他六个省份才只能分得剩下的名额。
以往其他州府的学子去明州府参加乡试时,遇到来自清河府的学子,谁不是羡妒有加?
这次盛大家要来安平省会讲,居然选了默默无闻的通州府学作为会讲活动举办地,他很是想不通,来之前便存了找茬的心,可此时却被谢景行不动声色地顶回来了,而且那话他怎么听都不对,却又找不到由头发作。
他觉得谢景行一定是装成这副平淡的样子,可是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谢景行同刚才大门那几位学子那样愤怒的情绪,甚至连其他表情都无。
赵朝贵找不到可拆穿的地方,不得不咽下这口气,恨恨地跟在谢景行身后。
而刚刚同谢景行对上视线的那位学子和葛夫子都很是看了他好几眼,眼神意味深长。
谢景行佯作不知,他若是知道赵朝贵心中的想法,也只会回他一句:“你想多了,同学。”
他前世可是全国顶级学府毕业,现在在通州府学读书,也有祝世维作为老师,祝世维原来可是翰林官,他实在用不着羡慕嫉妒他。
会说阴阳话,也是看不惯他无缘无故暗说府学的不是,无论如何,他都是府学的一员,集体荣誉感还是有的。
第134章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