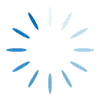这样该怎么办?如此好的提议,总不能因为人数不对等就放弃吧。
屿哥儿知道谢景行又是在逗他,不过仍然作势瞪了他一眼,这才难不住他,谢哥哥肯定也是有主意了,可就是不提醒他。
他自己也可以想到,他几乎是立即就道:“那就让你们自由选择想为我们文清院哪位学子的画作诗,到时再由我们文青院的学子和你们投票,看哪首诗更好,再将被选出的诗题在画上,这样如何?”
尽管知道谢景行在逗他玩儿,但是他仍有些紧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面前的谢景行,屏息凝神等他的回应。
谢景行终于将脸上笑意完全展开,道:“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眼看着屿哥儿的眼神里逐渐浮现出一丝羞恼,他才说出后面两个字,“可行。”
屿哥儿立即笑开了。
时梦琪手里拿着两个提篮,等他们商量好了,才看向屿哥儿,故意板着脸,说道:“你们这就决定了?都不用问问我们文清苑其他学子的意见吗?”
然后她又笑着回首看向身后的众女子哥儿,问道:“你们说是不是?”
通州府学可不只是汉子这边知道谢景行和屿哥儿的关系,文清苑的女子和哥儿们可比汉子们更早知道,就算有新入学的学子一开始不知,在其他人平日里的谈论中,也将之了解得很是清楚,更遑论谢景行和屿哥儿根本从未遮掩过,行事光明正大,日日同进同出,生怕人不知道是的。
这时时梦琪一问他们,大伙跟说好了一样,脸带笑意调侃地看向屿哥儿,有一位活泼些的女子当即应声,“是呀,我们的意见就不重要了吗?”
这次谢景行身后其他府的学子却未曾担心,明显看出那些女子哥儿是在说笑。
屿哥儿作为被捉弄的当事人,这才回想起他确实忽略了同窗们的意见,脸上顷刻间浮起红霞,显着那张精致的脸更是明艳灵动。
他坑坑巴巴着,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
温嘉方才一言未出,他也觉得屿哥儿的意见甚是好玩,不过此时大家都在捉弄屿哥儿,他当然也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拉着身旁的白苏和潘婧雪走到了前面,高声道:“就是,有人见到那谁后,就什么都顾不得了,我们又哪里会被他放在心上?说不定他早就忘了还有我们这一众同窗呢。”
连一下温婉善解人意的白苏和潘婧雪都未帮他搭腔,只含笑看着他。
这下在场的其他几府学子也看出端倪了,纷纷将视线在谢景行和屿哥儿身上来回游移。
最后,屿哥儿也将求助的视线投向了谢景行。
谢景行本来就已快有动作了,现在更是没有犹豫,抬步走到屿哥儿身旁,朝文清苑的学子们抬手一揖,“各位还请高抬贵手。”
屿哥儿这次真的是赧然汗下。
因为好不容易在府学里面看到谢哥哥,一时激动,居然全然没有询问同窗们的意见,擅自就做下了决定,属实不该。
脚尖往旁一挪,脚后跟陆续跟上,三两下就挪到了谢景行身后,将那张羞得红彤彤的脸蛋完全藏了起来。
谢景行心下好笑,当然脸上笑意也未褪去,坦然承受着这里近百人直勾勾的注视,一点不慌。
时梦琪和温嘉撇撇嘴,两人对视一眼,时梦琪挥了挥手,“算了,就这样决定吧。”她将手里屿哥儿的提篮递了过去,她已经帮着提了好一会儿了。
谢景行从她手中接过,她才走到丘逸晨身边,将提篮往他手上一放。
其他人本就是逗着屿哥儿玩儿,也都没有其他意见。
苏夫子看大家都同意了,便说道:“既如此,文清苑的学子们便自己寻一处合意的位置开始作画吧。”
通州府学建立时,初代山长考虑得很是周全,湖边除了有一处风响亭外,小道边还有着不少配套的石桌和石凳,方便府学中人散步累了时,随时可以坐下歇息。
有的石桌上面甚至还画有棋盘,若是有意,还可以自己带着棋子在湖边伴着美景手谈。
虽然觉得这种比赛很有意思,不过不少事先做了准备的学子心中还是有些发慌,毕竟谁又知道这些通州府学的女子哥儿们会不会画与自己准备好的诗有关的主题呢,不过,他们看了看身旁所有的人,不只是他们如此,其他人都是同样的情况,若是只凭真才实学,自己也不一定会输。
再说了,既然是在湖边作画,画中的风景不外乎就是湖、柳、荷,到时机灵点,多看看,说不定就能用上准备好的诗呢?
这么想着,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也有心思在湖边四处行走,想要观赏一下通州府学的女子哥儿的作画水平到底如何。
终于等到其他人没有多加关注屿哥儿和自己了,谢景行这才拉着身后的屿哥儿到了远处的一处石桌坐下,将他提篮里的一样样东西往外拿。
屿哥儿脸上的红晕好一会儿才消下去,有些埋怨地悄悄瞪了谢景行一眼。
谢景行刚一侧头,就发现了这羞恼的一眼,好笑问道:“怎么还怨上我了?”
屿哥儿理不直气也壮,“我在迁怒你呀。”
他心中默默想到:“也不算迁怒,若不是谢哥哥让他脑袋空空,他才不会做出忽略同窗意见的事情呢。”
他明明和同窗之间关系可好了,做事都是有商有量的,偏偏这次忽略了。
谢景行顺了顺他披散到肩头的发丝,“行,都是我的错,日头要大了,快画吧。”
屿哥儿用眼角看着他宠溺的侧脸,这里他最想画的就是谢哥哥了,不过若是画出来,肯定会招致这里所有人的嘲笑,他才不要。
不过,他扫了周围一圈。
有谢哥哥在旁边,其他的湖水、荷花,甚至是荷尖上的蜻蜓,他都提不起心思画。
将下巴磕在面前的石桌上,屿哥儿烦恼道:“到底该画什么才好?”
谢景行方才已将桌面擦得干干净净,由着他去了。
又抬头望了望头顶高大的柳树,幸亏石桌都在柳荫下,就算太阳有些烈,也没有太大影响。
屿哥儿往上抬眼看着谢景行眉目英挺的侧颜,轮廓像是被最好的画家细细勾描出来的,无一丝多余,处处都恰到好处,好看的不得了,这世上再没人能比谢哥哥长得更合他的心意了。
谢景行看着他的神情变化,心中发软。
不过别人都已经开始动笔了,这小哥儿还一直盯着他发呆,他伸出手指轻轻崩了他脑门一下,“别人都快画好了,你还不抓紧点。”
屿哥儿用手按住眉心,其实并不疼,不禁又想着,“谢哥哥哪里都好,就是有时不太解风情。”
可转瞬间又换了个念头,“不过这样也好,其他人不知道谢哥哥的好,就都不会与他抢。”
他仍然没动,不过眼神却往上看了看,碧蓝的天空上,一团又一团的白云映入他的眼帘。
屿哥儿眼神动了动,将头抬了起来,他想到可以画什么了。
谢景行见他开始动作,便就在一旁为他递笔拿墨,两人虽未曾交谈一言一语,可却仿若自成一体,任谁也插不进去。
一旁的其他汉子学子在四处观看女子哥儿作画时,不约而同地都避开了他们。
真有心找茬的赵朝贵和秦学子也都很有眼色,远远就绕开了他们,甚至心中还酸溜溜地想,“这谢景行还真是人生赢家呀!”
年纪轻轻才华过人,不出意外本次乡试定能中举,十八岁的举人,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而且还有佳人相伴!
哪哪都是他们所不及的,能不酸吗?
待会儿一定要在诗上压他一头,两人巧合地走在了一处,互相对视一眼,双眼冒出熊熊斗志。
谢景行正温柔看着屿哥儿,帮着他拿碟,然后看他将盒子里的不同染料倒在碟子里,又往里注入水,三两下就调成了清透的蓝色,他从一旁拿了一只着色笔,用笔尖在碟上沾了颜料,没有犹豫直接就将笔落在了宣纸上。
三两笔间,雪白的宣纸上就落下了一片浅蓝,右侧空着,他继续浓涂淡抹,大片大片的蓝色就绽放在宣纸上。
接着,他换过一支笔,又调了一点白色的染料,用笔细细勾抹,一团云彩便落在了那一抹蓝旁。
这还未曾结束,他又调了一叠赤金色,并未在画上画出灼灼烈日,而是以染料在云彩和蓝天上东抹西涂,蓝天白云便瞬间点染上了烈日的橙黄。
不过半个时辰不到,一幅晴天飘云图便被画了出来。
朗朗晴空,万里飘云,云彩又似从光间跃出,本该是一副静到极致的画面,却无端让人觉得蓝天云彩互相竞足。
唯独让人奇异的是,云朵只有一团,除此之外,就只剩碧蓝的晴空,再无其他。
不过屿哥儿却很满意,将手上的笔放下,他垂头欣赏自己刚刚完成的杰作,云就只该有一朵,就像这天下间谢哥哥也只有一个一样。
谢景行看着他在那里风流自赏,不觉得好笑,反倒觉得他很是可爱,或许在其他人看来,这幅画并不是多好,不过只要是出自屿哥儿之手,他便觉得是极好的。
时梦琪早已画完,她将画推至丘逸晨眼前,让他开始想诗,这点她还是有自信的,丘逸晨想都别想去为其他人的画作诗。
溜溜哒哒到了谢景行和屿哥儿所在的石桌前,别说她没有眼色,她就是好奇。
同为文清苑学子,她当然是知道屿哥儿画画的实力,在整个文清苑之中,屿哥儿的画技只能算是中等偏下。
文清苑学子也常互相比斗,一开始是比诗比文,比花比茶等等,有羽毛球之后,也会比羽毛球。
比赛的项目还不少,可不论是比作诗,还是比作文,甚至是比羽毛球,文清苑大多数人都是比不过屿哥儿的。
不少文清苑学子都会在屿哥儿这里受挫,有不服输的学子想要找回场子,就会抓着屿哥儿比作画,比下棋,这两项都是屿哥儿的弱处。
一看到石桌上宣纸上的画,时梦琪噗嗤一笑,“这里有这般多好画的景物,你偏要选蓝天白云,选这个也就算了,你这云还只有一朵,你不觉得这朵云很是孤单吗?”
屿哥儿摇头,“不觉得。”
他没有多搭理时梦琪,而是转头问身旁的人,“谢哥哥,你觉得它会孤单吗?”
谢景行也摇头,温声道:“不是有蓝天陪着它吗?”
时梦琪就多余问这一句,这两人成双成对的,哪里会觉得孤单,不过她又问:“可这只有一朵云在碧蓝的天空上,你让谢景行怎么做诗,这可不好作。”
她是女子,声音比男子更为尖细,声音传得远,不少他处的学子也听见了,见有人在谢景行两人身旁,也跟着过来了,都往石桌上的画看去,然后纷纷蹙眉。
确如这名女子所说,只是一朵孤云,想要为其作诗,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头绪。
就连韩回舟也在眉间拢出了一道细纹,他也没有灵感。
看其他人纷纷被难住,屿哥儿这才意识到他这可不只是自己作画,还得让谢哥哥为这幅画题诗呢。
他也是会写诗的,甚至在谢景行数不清的华夏诗的熏陶下,写的诗还非常不错,他意识到这回事之后,眼里涌起了一丝困扰,就是他自己,一时也没想到该如何为这幅画作诗。
屿哥儿眨巴眨巴圆圆的猫眼,看着谢景行,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怎么就为谢哥哥出了这么一道难题?
不少人看向谢景行的眼神带上了一丝同情,丘逸晨也来凑热闹了,他更是直接,拍着谢景行的肩膀同情道:“谢兄,我们还可以去寻有灵感的画作诗,可你...”
他看向面前眼巴巴看着谢景行的屿哥儿,同情瞬间变成幸灾乐祸,笑道:“就自求多福吧。”
他可还记得自己刚才是被谁拖下水的。
边上围着他们的人纷纷离开了,又只剩下了谢景行和屿哥儿。
有的人已经将笔拿在了手里,而文清苑的学子们带过来的纸也不少,便各自寻了地方为自己选中的画作诗。
可是好一会儿过去,谢景行还是毫无动作,仍然直直盯着石桌上的画。
屿哥儿这下是真的有些急了,难道谢哥哥也想不到吗?担心地看着谢景行,屿哥儿道:“要不我重新画一张?”他抬头看向快到头顶的太阳,“应该来得及的。”
谢景行伸出手揉揉他急得快炸毛的头发,安慰道:“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吗?”
他话里的意思很是明确,屿哥儿只要得到他透露的一点点意思便立即安下心,脸上重新露出笑意,“谢哥哥说行就一定可以的。”
这次轮到他为谢景行研墨了,从一旁的篮子中面拿出一个小碟子,他们今日是来作画的,许多人都没有带重量不轻的砚台,不过碟子也可以凑合一下。
不多时,墨汁便被研墨好了,从一旁取出一支硬豪笔,谢景行拿笔在碟中沾了墨,沉吟片刻,便在画的右侧空白处提笔写下两个字:“孤云”。
笔锋凌厉,运笔流畅,只是两字就足以见谢景行写字的功底。
至于谢景行为什么不向其他学子那样,拿另一张纸出来写诗,自然是因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来自讨没趣,偏要插在一对有情人之间。
就算真有那的没眼色之人,可屿哥儿的画极有难度,任谁也不会来自讨苦吃。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